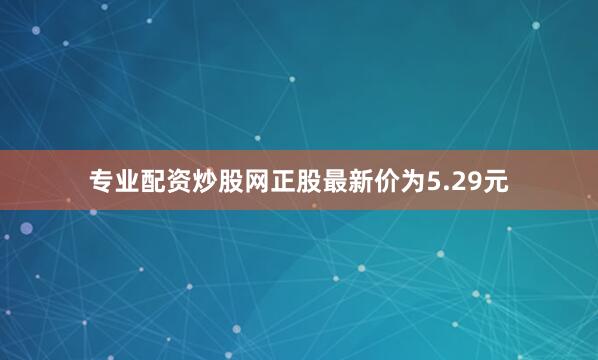“徐海东送5000大洋解中央燃眉之急,这事大家都知道!”
党史讨论会上,有人感慨。
一旁老研究员却摇头:
“那只是其一,他还有个比5000大洋更重要的大恩。”
“比救命钱还重要?”
01
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自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启程,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这支由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及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共同领导的部队,人数不足三千,被中共中央赋予“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使命。
彼时,红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的通讯联络已中断,其行动既无上级直接指令,亦无友军策应,实属孤军深入。
在随后的行军过程中,部队需穿越敌军重兵布防区域,面对国民党军三十余个团的围追堵截,其处境之艰险,可见一斑。
在该军主要领导人物中,徐海东的经历尤为引人注目。
他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一个世代以烧窑为业的家庭,自幼随父辈从事窑工劳动,前后长达十一年。
窑场环境恶劣,劳动强度极大,这段经历不仅锤炼了其体魄,更塑造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
1925年,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投身革命洪流。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他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
因其作战勇猛、指挥果断,被当地军民称为“徐老虎”。
值得注意的是,徐海东的革命道路并非坦途。
据史料记载,在其投身革命后,家族遭受严重打击,多达六十六位亲属因“通共”罪名被地方反动势力杀害。
面对如此惨烈的家庭牺牲,徐海东并未动摇信念,反而更加坚定了其革命意志。
他曾对身边同志坦言:“亲人的血不能白流,唯有彻底推翻压迫,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这种将个人悲痛转化为革命动力的心理机制,在当时许多红军将领中具有典型性。

在军事实践中,徐海东素以身先士卒著称。
据其战友回忆,在多次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九次负伤,全身留有十七处伤疤。
其中最为惊险的一次发生于1933年的一场突围战中,一颗子弹贯穿其左腿,血流不止,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完成战术任务。
此类事例不仅体现了其个人英勇,也反映出当时红军指挥员普遍具有的牺牲精神与责任意识。
红二十五军虽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士气高昂。
部队中多为鄂豫皖地区出身的青年农民,政治觉悟较高,战斗意志坚定。
在缺乏外部支援、信息闭塞的条件下,军领导层依靠集体决策与群众路线,维系了部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战士们对徐海东等指挥员的信任,并非仅源于其军事才能,更在于其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
有老兵回忆:“徐副军长吃饭和我们一样,行军时也从不骑马,伤还没好就跟着队伍走。我们信他,是因为他真把我们当兄弟。”
02
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自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后,即陷入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围堵体系之中。
该部作为中共中央指定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在与中央失去联络、缺乏外部策应的孤立状态下,被迫在敌强我弱的极端环境中展开战略转移。
其行军路线横贯豫西南,途经桐柏山、伏牛山等复杂地形,沿途遭遇国民党军三十余个团的轮番围追堵截,形势异常严峻。
其中,1934年11月26日于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爆发的战斗,被后世史家普遍视为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最为危急的一役。
当日正值严冬,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部队行进至独树镇七里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庞炳勋部预设伏击。
由于先头部队未能及时察觉敌情,猝然接敌后陷入被动,伤亡迅速扩大。
据《红二十五军战史》记载,战斗初期,红军一度被压制于开阔地带,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突发危机,军领导层迅速作出反应。
副军长徐海东亲率一支由骨干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密集火力发起反冲锋。
据亲历者回忆,徐海东在冲锋前曾对战士们简短动员:
“现在退就是死,冲出去才有活路!”此举极大提振了士气。
在指挥员身先士卒的带动下,红军战士奋勇拼杀,于次日拂晓成功撕开敌军包围圈,实现战术突围。
然而,此役代价惨重,全军减员近三分之一,部分连队几近覆没,武器弹药亦严重损耗。

独树镇之战的惨痛教训,促使红二十五军在战术层面进行深刻反思。
此后,部队显著加强了侦察警戒制度,行军时多设前哨、侧翼警戒,并注重利用地形隐蔽行动。
同时,指挥层开始强调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避免与敌主力正面硬拼,转而采取“避实击虚、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
这一战略调适,成为其后续在伏牛山区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
进入伏牛山区后,地理环境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生存压力。
该区域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冬季气候严寒,补给线完全中断。
据档案资料记载,部队一度断粮数日,战士们以野菜、树皮充饥,饮雪水解渴。
在此极端条件下,部队纪律与凝聚力却未见涣散。相反,官兵之间互助共济的现象屡见不鲜。
徐海东虽身为高级指挥员,仍坚持与普通战士同食同宿,多次将有限的干粮分予伤病员,并在夜间主动承担站岗任务。
有老战士回忆:“徐副军长把棉衣让给伤员,自己裹着破毯子睡觉,谁看了不心疼?”
1934年12月初,红二十五军翻越秦岭,进入陕南地区。
03
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西省商洛地区今丹凤县庾家河镇,并于次日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
此次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中具有关键意义,
会议通过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正式决定以陕南为中心,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决策的作出,正值部队历经独树镇血战、伏牛山艰难跋涉之后,
人员减员严重、物资极度匮乏、对当地社会环境尚不熟悉,其战略判断之果断与政治视野之深远,
体现出红二十五军领导集体在极端困境下的高度政治自觉与战略定力。
从历史背景看,该决策并非仓促之举,而是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与自身处境的综合研判。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
而红二十五军作为先遣部队,肩负着“牵制敌军、开辟通道、建立支点”的多重任务。
进入陕南后,部队发现该地区地处秦岭腹地,山势险峻、交通闭塞,
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且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受压迫深重,具备开展土地革命与群众动员的社会基础。
在此背景下,省委果断放弃继续西进或南下的设想,转而立足陕南,实施“就地扎根、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战略方针。
根据地创建初期,红二十五军采取“武装开路、政治跟进”的双轨策略。
一方面,部队继续以军事行动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如民团、保安队及土豪劣绅控制的武装力量,迅速肃清周边敌对势力;
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
据《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记载,红军每到一地,即组织宣传队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讲解“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救国”等主张。
一位当地老人回忆:“红军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我们挑水砍柴,和以前见过的兵完全不一样。”
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红二十五军同步推进土地革命。
1935年初,部队在镇安、山阳、柞水等地试点开展土地分配,没收地主豪绅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给贫雇农。
此举迅速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不仅巩固了社会基础,也为兵员补充提供了来源。
据档案统计,至1935年春,仅镇安县就有三百余名青年加入红军或地方赤卫队。
与此同时,部队注重统一战线策略,对开明士绅、地方知识分子采取争取与团结政策,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例如,在蓝田县,红军曾邀请当地乡绅参与临时苏维埃筹备会议,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初期的敌对情绪。
在政权与组织建设方面,红二十五军亦展现出较强的制度建构能力。
1935年2月,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今属湖北,时属陕南游击区)成立陕南特委,并陆续在根据地核心区域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
同时,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组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武装组织,形成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的军事体系。
经济上,部队尝试恢复集市贸易,设立临时粮站,保护小商贩利益,
并在条件允许的地区组织互助耕作,以缓解战时经济压力。
04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稳固、部队兵员恢复至三千余人、地方政权与群众基础日益巩固的背景下,面临一次关乎战略方向的重大抉择:
是继续留守陕南,深耕既有根据地,还是主动放弃局部成果,挥师北上,向陕甘边区进发。
这一决策不仅关系到红二十五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路径,更在客观上对中国革命整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现实条件看,留守陕南确具合理性。
自1934年12月进入陕南以来,红二十五军通过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
已在镇安、山阳、柞水、蓝田等地形成较为连片的游击区域,群众支持度较高,地方武装体系初具规模。
部队经过半年休整,战斗力明显恢复,且远离国民党军主力围剿中心,具备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然而,以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为核心的军领导层并未局限于局部利益,
而是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对战略前景进行了深入研判。
据《红二十五军战史》及鄂豫陕省委会议记录显示,
1935年7月中旬,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专题讨论战略转移问题。
会上,部分干部主张“巩固现有成果,稳步发展”,但徐海东等人指出:
陕南地域狭小,回旋余地有限,且地处秦岭腹地,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红军主力;
而陕甘边区地域广阔,与宁夏、甘肃接壤,战略纵深更大,且已有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在此坚持斗争,具备联合发展的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通过缴获的敌方报纸与零星情报,判断中央红军在川康地区处境艰难,极有可能向西北转移。
若红二十五军率先抵达陕甘,不仅可实现红军主力会师,更能为中央提供落脚点与物资支援。
这一判断虽缺乏直接电讯佐证,却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前瞻性。
事实上,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已开始酝酿北上方针;
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正式确立“向陕甘进军”的战略方向。
红二十五军的决策,恰与中央战略意图形成历史性的契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长安县沣峪口出发,开始第二次战略转移——北上陕甘。
部队轻装简从,昼伏夜行,穿越关中平原,突破国民党军多道封锁线。

途中虽遭遇多次阻击,但凭借灵活机动战术与群众掩护,于9月15日抵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
而当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永坪镇那一刻,
徐海东望着眼前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心中涌起的那个想法,将彻底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05
而当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永坪镇那一刻,
徐海东望着眼前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心中涌起的那个想法,将彻底改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那一刻,秋风萧瑟,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尘土飞扬,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却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徐海东站在队伍前列,身上那件褪色的军装布满尘土,左腿的旧伤隐隐作痛,但他没有一丝退缩。
他望着对面那支同样饱经风霜的陕甘红军,刘志丹那张坚毅的脸庞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轮廓分明。
徐海东心想:“我们终于来了,这里将是革命的新起点。我们必须站稳脚跟,为中央红军开辟道路。”
这个念头如火炬般点燃了他的斗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两支红军的会师,更是整个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点。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
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部队,自1934年11月启程以来,已跋涉近万里,穿越河南、陕西的崇山峻岭,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
抵达陕北时,全军人数虽不足三千,但每一名战士都如钢铁般坚韧。
陕甘边区的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早已得到情报,亲率部队前来迎接。
两军会师的场景令人动容:陕甘红军的战士们手持红缨枪,身上裹着羊皮袄,脸上是高原风沙雕琢出的沧桑;
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则多是南方口音,衣衫单薄,却精神饱满。
双方战士相拥而泣,互诉长征的苦难与胜利。
刘志丹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
“徐副军长,你们来得正是时候!陕甘根据地虽有基础,但国民党围剿日益加紧。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徐海东点点头,目光坚定:“刘政委,我们红二十五军北上,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壮大革命力量。
陕北地广人稀,回旋余地大,我们必须在这里站稳脚跟。”
这一刻,两支红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的首次大规模联合。
它不仅结束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征程——这支部队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主力——更在陕北这片黄土高原上点燃了革命的燎原之火。
会师后,双方迅速展开整编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实际情况,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徐海东出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这一合编极大增强了陕北红军的实力。
原本陕甘红军人数有限,仅有数千人,且装备简陋;
红二十五军的加入,不仅带来了精锐的战斗部队,还带来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和组织体系。
全军团人数迅速扩充至七千余人,形成了三个师的建制:
红七十四师、红七十五师和红七十八师。
这支新军团的成立,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陕北根据地的活力。
陕北根据地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
国民党蒋介石为剿灭西北红军,调集了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总兵力达十余万,层层封锁陕甘宁边区。
红十五军团的首要任务,便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
徐海东作为军团长,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
他深知,陕北地形复杂,多沟壑梁峁,适合游击战,但也易被敌人分割包围。
因此,他强调“机动灵活、避实击虚”的战术原则,指挥部队开展了一系列战斗。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役便是劳山战役。

1935年10月,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
纠集两个团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核心区域劳山推进,企图一举摧毁红十五军团的指挥中枢。
劳山位于延安以北,地势险要,四周环山,易守难攻,但国民党军仗着人多势众,采用步步推进的战术,意图将红军压缩在狭窄地带。
徐海东得到情报后,立即召集军团会议。
刘志丹建议:“敌人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拼,得利用地形设伏。”
徐海东赞同道:“对!我们分兵诱敌深入,主力和陕北游击队从侧翼包抄。记住,保存实力是第一位。”
他亲自绘制作战图,分配任务:红七十五师佯装败退,引敌进入劳山峡谷;红七十四师埋伏在山梁两侧,待敌疲惫时发起总攻。
10月7日,战斗打响。国民党军果然中计,牛元峰部骄横推进,进入峡谷后陷入红军的伏击圈。
徐海东亲临一线指挥,他骑着一匹瘦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喊道:
“同志们,冲啊!打垮他们,陕北就是我们的!”
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机枪、手榴弹齐发,国民党军阵脚大乱。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红十五军团以少胜多,全歼敌一个团,生俘牛元峰以下官兵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此次胜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还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
陕北农民纷纷加入红军或赤卫队,根据地迅速扩大到二十余县,人口达百万之众。
劳山战役的胜利并非孤立事件。
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红十五军团随后又取得了一系列胜仗,如榆林桥战斗和直罗镇战役。
这些战斗进一步巩固了陕北根据地。榆林桥位于甘泉县境内,国民党军企图以此为据点切断红军的补给线。
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夜袭榆林桥,摧毁敌桥头堡,俘敌数百。
直罗镇战役则发生在1935年11月下旬,这是红十五军团与刚刚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仗,但在此之前,红十五军团已通过劳山等役稳住了阵脚。
徐海东在这些战斗中,始终强调与群众的紧密联系。
他下令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抢粮,甚至帮助农民收割庄稼。
这赢得了陕北人民的衷心拥护,许多窑洞里流传着“徐老虎来了,蒋匪要跑了”的歌谣。
通过这些军事胜利,陕北根据地从一个薄弱的游击区,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稳固的革命堡垒。
土地革命在这里深入开展,红十五军团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建立苏维埃政权,推行识字班和互助组;经济上,恢复窑洞生产,发展手工业,避免了饥荒的威胁。
徐海东亲自参与根据地建设,他常常深入基层,与战士和农民交谈。
有一次,在一个窑洞会议上,他对同志们说:“我们不是来占地盘的,是来为人民服务的。陕北稳了,中央来了就有落脚点。”
他的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也为中央红军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
这支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有八万余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七千余,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无数磨难,体力已到极限。
如果陕北根据地此时仍处于动荡之中,中央红军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但得益于红二十五军——现红十五军团——的先期抵达和巩固工作,
陕北已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稳固的落脚点。
中央红军抵达时,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主力前来迎接。
毛泽东握着徐海东的手,感慨道:
“徐海东同志,你们红二十五军是先遣队,更是开路先锋!
没有你们先稳住陕北,我们的落脚点从何而来?”
徐海东谦虚地笑了笑:
“毛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陕北人民和我们一起打下了这片江山。”
会师后,中央红军迅速休整,补充兵员,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中心。
从此,中共中央在这里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最终走向新中国成立。
徐海东对中央的这个“大恩”,远比送5000大洋更重要。
那5000大洋,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从红十五军团的有限资金中挤出,送给中央以解燃眉之急。这件事广为人知,被誉为“雪中送炭”。
但实际上,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先期抵达陕北,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才是真正奠定革命全局的基础。

如果没有红二十五军的北上和会师,陕北红军力量薄弱,很可能在国民党围剿中瓦解;
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将无处安身,革命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正如党史专家所言:
“5000大洋是救急之资,而陕北根据地是革命之基。徐海东的功劳,在于为中央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回顾徐海东的革命历程,这个“大恩”并非偶然。
他从窑工出身,历经家族惨案、九死一生,却始终坚定信念。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中,他身先士卒,指挥独树镇突围、劳山歼敌,每一步都体现出战略远见。
陕北的稳固,不仅是军事胜利的结果,更是政治智慧的结晶。
徐海东强调统一战线,争取当地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支持,避免了内部矛盾;
他注重情报工作,通过缴获敌报,预判中央动向,主动北上。这些细节,构成了逻辑自洽的革命链条。
若没有徐海东部先稳固陕北,很难说这里能否成为中央红军的可靠落脚点。
假设红二十五军未北上,陕甘红军孤立无援,国民党围剿得逞,中央红军抵达时将面临四面楚歌。
历史不会重演,但从常理推断,陕北的丢失将导致革命低谷延长,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将延缓。
徐海东的贡献,正是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乾坤。
陕北会师后,徐海东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1936年,红十五军团参与东征战役,渡过黄河,打击阎锡山部,扩大根据地。
徐海东指挥红七十五师,在山城堡战斗中大败敌军,缴获大量武器。
这次战役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安全环境。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
徐海东的个人品格,也在陕北时期得到充分体现。他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化。
一次,部队缴获一批棉布,他优先分给战士,自己仍穿旧衣。
战士们说:“徐军长像大哥一样。”他的伤疤,成为激励后辈的勋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旅长,继续浴血奋战。
在党史中,徐海东的“大恩”被多次提及。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赞扬:“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有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但他谦虚地说:
“这是党的功劳。”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
扩展到更广的视野,徐海东的贡献体现了中国革命的集体智慧。
红二十五军的北上,是中共中央战略的一部分,但徐海东的执行力,使其成为现实。
陕北根据地的巩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军事上,劳山等战役打破围剿;
政治上,土地革命赢得民心;经济上,自力更生避免崩溃。
这些环节环环相扣,逻辑严密。
如果深挖历史细节,红二十五军在陕北的行动还包括情报网络的建立。
徐海东派小分队潜入西安,获取国民党动向,这为后续战斗提供了先机。
群众工作方面,他组织“红色剧社”,用文艺形式宣传革命,增强凝聚力。
这些举措,都符合现实常理: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红军靠人民支持生存。
陕北根据地的稳固,对中国革命全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不仅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还成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
从1935年到1947年,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吸引无数知识分子和青年投身革命。
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合作。
徐海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他不只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在红十五军团内部,他推动整顿纪律,清除“左”倾错误,确保部队纯洁。
一次,面对内部争论,他说:“革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是集体的事业。我们为中央稳住陕北,就是最大的贡献。”
对比5000大洋,那不过是物质援助,而陕北根据地是战略基石。
5000大洋能解一时之急,但根据地能支撑长期斗争。
没有根据地,中央红军将流离失所,革命火种难存。徐海东的“大恩”,在于预见性和执行力。
他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判断中央北上意图,主动行动,这体现了革命者的担当。
历史假设虽不可靠,但从逻辑推演:
若红二十五军滞留陕南,陕北红军难敌围剿,中央红军或被迫西进新疆,革命将遭受更大损失。
徐海东的决策,避免了这一悲剧。
徐海东的革命生涯,还延伸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
1949年后,他担任军区司令,参与剿匪和边防建设。尽管健康欠佳,他仍坚持工作。
1970年逝世时,全国哀悼。
他的遗著《生平自述》,详述了陕北经历,强调集体功劳。
在当代,徐海东的故事被编入教材,激励青年。
党史讨论会上,那位老研究员的话,正是点明这一“大恩”。
5000大洋是显性贡献,陕北稳固是隐性伟业。
徐海东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的缩影:坚韧、远见、奉献。
它提醒我们,革命成功靠无数无名英雄的积累。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并非真实历史,未涉及宗教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参考资料:[1] 《红二十五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2]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3] 《徐海东生平自述》. 解放军出版社.[4]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东南配资-实盘杠杆配资平台-配资平台下载-国内大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杠杆平台app哪个可靠全面守护脑健康和神经系统健康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