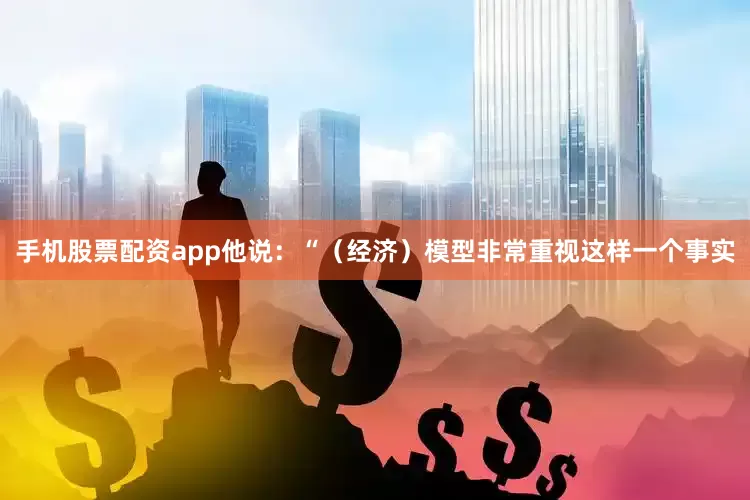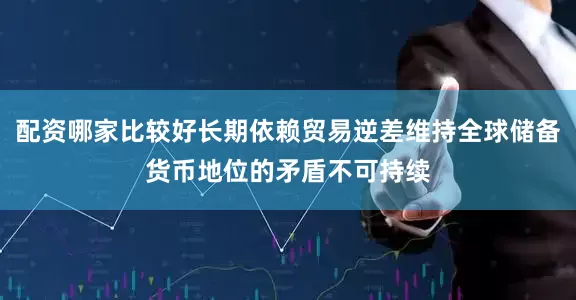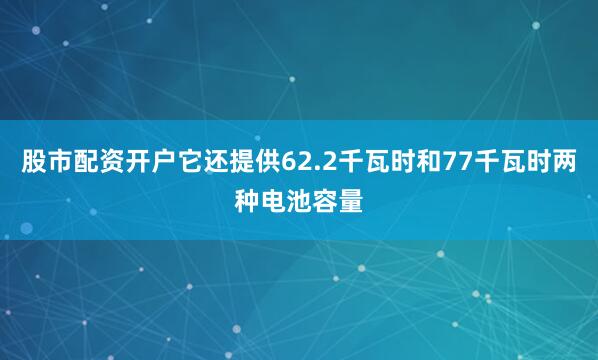01
1935年9月16日,夜,甘肃迭部县,俄界。
空气湿冷,浸透了单薄的军衣,钻进骨头缝里。油灯的光晕在低矮的土屋里摇曳,将墙壁上几个巨大的人影投射得如同鬼魅。
彭德怀坐在一条长凳上,双肘支在膝盖上,那双习惯于紧握马缰和枪柄的大手,此刻正深深地插入他那乱蓬蓬的头发里。他已经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面前桌上铺开的简陋地图。
地图是用铅笔和红蓝墨水画在粗糙的麻纸上的,上面的线条,代表着山脉、河流,以及此刻正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的,数倍于己的敌军。
「军团长,」一个沙哑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不能再等了。」
彭德怀缓缓抬起头,看向说话的人。是叶剑英,时任陕甘支队参谋长。他的面容一如既往地沉静,但镜片后面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却透着一股化不开的凝重。
就在几个小时前,最坏的消息被证实了。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公然南下,不仅带走了红军的主力,也带走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补给。此刻,跟随着中央北上的,只有彭德怀麾下的红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而成的陕甘支队,总兵力不足八千人。
八千人,衣衫褴褛,弹药匮乏,饥肠辘辘。他们刚刚从死亡的草地里爬出来,许多战士的腿上还裹着溃烂的脓疮。
而他们的面前,横亘着一道天险——腊子口。
02
「是个口袋。」
彭德怀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低沉而嘶哑。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重重一点,那个被标记为“腊子口”的地方,仿佛一个狰狞的兽口。
「两边是无法攀爬的绝壁,中间只有一条三十米宽的隘口,一道小木桥。国民党鲁大昌的第十四师一个营守在那里,居高临下,轻重机枪、手榴弹……我们这点人,拿什么去填?」
屋内一片沉默。
所有人都知道,彭德怀说的不是气话,而是冰冷的事实。强攻,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支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百战之师,很可能就要在这里,在这片荒凉的甘南山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叶剑英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缓缓开口。
「绕路呢?我们研究过,从腊子口西侧的山地绕过去,至少要多走七天。七天,我们的粮食撑不住,鲁大昌的援军也早就把我们包围了。」
他的话语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不打,是等死。打,是找死。
这就是陕甘支队此刻面临的绝境。
彭德怀站起身,在狭小的土屋里来回踱步。他的军靴踩在泥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在叩问着这片沉默的土地。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随着他。他们知道这位军团长的脾气,山一样坚毅,火一样爆裂。他从不畏惧任何强大的敌人,但此刻,他脸上的神情,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挣扎。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战斗,这是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之战。他肩上扛着的,是这七千多条性命,更是中国革命仅存的火种。
03
突然,彭德怀停下脚步,目光转向了土屋角落里一个始终没有说话的人。
那人穿着一身同样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材高大,面容清癯,正就着昏暗的灯光,专注地看着一份文件。他似乎完全没有被屋内紧张到窒息的气氛所影响,只是偶尔会用指节,轻轻叩击一下桌面。
「政委,」彭德怀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寻,「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缓缓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他的目光平静而深邃,仿佛能穿透这沉沉的黑夜,看到遥远的未来。
他没有直接回答彭德怀的问题,而是拿起桌上的一个搪瓷缸,喝了一口已经冰凉的开水,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彭德怀同志,我问你,我们从江西出来,为的是什么?」
彭德怀一怔,这个问题太大了。为了北上抗日?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
似乎都对,但似乎又都不完全。
毛泽东看着他,继续说道:「为的是活下去,走到一个能让我们喘口气、扎下根的地方去。现在,这个地方就在前面,过了腊子口,就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我们自己的根据地。」
他的声音不高,却有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
「腊子口,是鬼门关,但也是我们唯一的生门。这个险,我们冒也得冒,不冒也得冒。」

彭德怀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我不是怕冒这个险!」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他特有的火气,「我是怕弟兄们白白牺牲!政委,你是做政治工作的,我是搞军事的。账不是这么算的。强攻,我们就算能打下来,还能剩下几个人?这点家底,我们赌不起!」
这是典型的彭德怀。在军事问题上,他有着绝对的权威和不容置喙的固执。他可以和任何人拍桌子,哪怕是眼前这位党的实际领袖。
04
屋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
毛泽东与彭德怀,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他们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这支军队的命运。这种直接的军事分歧,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动怒。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彭德怀,眼神里甚至还带上了一丝笑意。
「德怀同志,你说的对,账不能这么算。」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
「你说的,是把鸡蛋往石头上碰。但我们偏不这么干。」
他的铅笔尖,在腊子口隘口旁边的悬崖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鲁大昌以为这里是绝壁,无人可以攀登。我们的战士,连雪山都爬上去了,这小小的山崖,又算得了什么?」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的意见是,正面佯攻,精兵奇袭。派一个小分队,从这个地方,趁着夜色,偷偷爬上去,摸到敌人的背后去。等山顶的枪声一响,正面部队就给我全力总攻!」
「这……」一位师长面露难色,「政委,这太冒险了。万一……」
「没有万一!」毛泽东打断了他,语气变得斩钉截铁,「军事,本身就是冒险的艺术。当年在红三军团,尚昆同志和你搭档的时候,你们打的险仗还少吗?」
彭德怀的心猛地一震。
杨尚昆,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许多往事。那是1934年,性格温和、细致周到的杨尚昆担任红三军团政委。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负责军事冲锋,一个负责政治动员,配合得天衣无缝。无数次在最艰难的时刻,都是杨尚昆那份沉稳和坚韧,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彭德怀的脾气火爆,全军闻名,但杨尚昆总能用他那春风化雨般的方式,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彭德怀后来常常说,杨尚昆教会了他很多,尤其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大局上。
而杨尚昆,这位比他小9岁的搭档,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一位真正的正国级领导人。
05
思绪只是一闪而过,彭德怀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眼前的地图上。
毛泽东提到的“奇兵”战术,确实是眼下唯一的破局之法。但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近乎完美的执行力。
「参谋长,」彭德怀转向叶剑英,「你觉得可行性有多大?」
叶剑英一直在仔细地听,此刻他沉稳地回答道:「可以一试。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找到合适的攀爬路线;第二,挑选出最精锐的突击队。攀爬路线需要派侦察兵连夜去摸,突击队,我看,就从一军团调一个最能打的连队来。」
彭德怀点了点头。叶剑英的思路总是如此清晰、周密。
这位被誉为“儒帅”的参谋长,是他军旅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搭档。原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战役中不幸牺牲后,叶剑英临危受命,来到了他的身边。
和那些能征善战的猛将不同,叶剑英更像一位运筹帷幄的谋士。他极少独当一面指挥大兵团作战,却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最清醒、最准确的判断。他的到来,给了脾气急躁、容易冲动的彭德怀一个极好的补充。彭德怀负责决断和冲锋,叶剑英则负责完善计划,拾遗补缺。
这种默契,在此刻的生死关头,显得尤为珍贵。
叶剑英,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担任过全国人大委员长,同样是正国级。
彭德怀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更多熟悉的面孔。
李富春,也曾是他的政委。当年,正是热心的李富春,将浦安修介绍给了他,成就了一段革命姻缘。李富春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国级。
还有刘少奇。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后来成为国家主席,被确立为接班人的理论家,在红军时期也曾担任过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与彭德怀近距离共事。尽管时间不长,但刘少奇那强大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也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个名字,一个个身影,都曾是他革命道路上最亲密的战友和搭档。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后来都登上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峰。
彭德怀猛然意识到一个过去从未深思过的问题:为什么和自己搭档过的人,后来都能达到如此之高的高度?
或许,这不仅仅是巧合。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在整个军队乃至全党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核心。只有最优秀的政治干部、最出色的参谋人才,才会被派来与他搭档,共同执掌这支最精锐、最能打硬仗的部队。

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政委,更是其中的“顶配”。
06
「好!」
彭德怀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声响让油灯的火焰都跳动了一下。
「就按政委的意见办!参谋长,你立刻去安排侦察和挑选突击队。其他人,分头去动员部队,准备打一场恶战!」
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火焰。
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光芒,一种属于“彭大将军”的,一往无前的决绝和霸气。
命令被迅速传达下去。整个营地,仿佛一头沉睡的狮子,在沉沉的黑夜里,悄然苏醒。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雷厉风行的背影,嘴角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他知道,只要彭德怀这把最锋利的战刀下定了决心,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他重新坐回桌边,却没有再看文件,而是陷入了沉思。
他与彭德怀,一个是放,一个是收;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战略家,一个是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他们的性格差异巨大,甚至时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然而,也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补。
他们都拥有着对中国革命最赤诚的忠心,和一颗永不言败的强大心脏。在长征这条血与火铺就的道路上,他们早已是生死相依、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却又缓缓放下。
今夜,注定无眠。
他要在这里,等着前线的消息,等着黎明的到来。
07
夜色如墨,山风如刀。
腊子口隘口前,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湍急的腊子河水,拍打着岩石,发出沉闷的轰鸣。
悬崖的峭壁上,几个黑影,如同壁虎一般,正艰难地向上攀爬。他们口中衔着短刀,身上除了武器弹药,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负重。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敌人的枪口。每向上一步,都是在向死神挑战。
带队的连长,名叫毛振华,是一个年仅19岁的贵州小伙子。他的身手最为矫健,像一只猿猴,在前面探路。
突然,他脚下一块岩石松动,身体猛地向下一坠。
跟在后面的战士们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
毛振华在半空中用尽全力,将手中的绳索奋力一甩,套住了上方一棵从石缝里顽强生长出来的小树。身体的下坠之势被止住了,但他整个人也悬在了半空,剧烈地喘息着。
崖顶上,国民党守军的哨兵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探出头来,用探照灯向崖下扫来。
刺眼的光柱,像一把利剑,划破了黑暗。
毛振华和他的队员们,一瞬间都僵住了,紧紧贴在冰冷的岩壁上,连呼吸都停止了。
光柱在他们身边几米远的地方来回扫过,每一次晃动,都让战士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个世纪,那道光柱终于移开,崖顶的哨兵嘟囔了一句“妈的,又是猫头鹰”,便缩回头去。
一场虚惊。
毛振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着身后的战士们做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手势。
他们,是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他们的成败,关系到整个部队的生死存亡。
与此同时,在腊子口的正前方,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佯攻部队,也已经悄然就位。
他举着望远镜,注视着对面黑沉沉的碉堡,手心已经满是汗水。
他一生指挥过无数次战斗,但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感到紧张。
这不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这更像是一场与天争命的豪赌。
08
凌晨四点,约定的时间到了。

彭德怀看了一眼身边掐着秒表的叶剑英,叶剑英对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打!」
彭德怀一声令下。
刹那间,沉寂的峡谷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和枪炮声。
几挺仅有的重机枪,向着敌人的碉堡喷吐出愤怒的火舌。战士们如同潮水一般,向着那座独木桥发起了冲锋。
然而,敌人的火力远比想象的要猛烈。
碉堡里的机枪,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网,冲上去的战士,一排排地倒下。手榴弹如同雨点般从天而降,在桥面上炸开一团团致命的火光。
第一次冲锋,失败了。
第二次冲锋,又失败了。
看着自己的士兵在敌人的火网下伤亡,彭德怀的心在滴血。他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眼睛因为愤怒和焦虑而变得通红。
「军团长,不能再这么冲了!」一名团长冲过来,大声喊道,「这是拿人命在填啊!」
彭德怀一把将他推开,嘶吼道:
「我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必须为山顶的同志争取时间!」
他很清楚,正面的牺牲越大,侧翼奇袭的成功率就越高。
可是,山顶上,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难道,奇袭分队出事了?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如果奇袭失败,那这所有的牺牲,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他抬头望向那黑漆漆的悬崖,心中第一次,产生了一丝动摇。
难道,这一次,我们真的要走到绝路了吗?
就在这时,一名通讯兵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
「报告军团长!政委……政委他……」
彭德怀的心猛地一沉,一把抓住通讯兵的衣领。
「政委怎么了?快说!」
通讯兵喘着粗气,几乎是哭着喊了出来。
「政委带着警卫排,从东边的河滩地,亲自带队冲锋了!」
09
「什么?!」
彭德怀如遭雷击,大脑一片空白。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毛泽东,党的领袖,亲自带队冲锋?这是何等的荒唐!这是何等的胡闹!
「他疯了吗?!警卫员呢?都干什么吃的!」彭德怀暴跳如雷,一把推开通讯兵,就要亲自去把毛泽东拉回来。
叶剑英一把拽住了他。
「老彭!你冷静点!」
叶剑英的脸上也满是震惊,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着镇定。
「政委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你现在过去,前线指挥怎么办?」
「道理?有什么道理!」彭德怀甩开叶剑英的手,双眼赤红,「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向全军交代?!」
愤怒,担忧,后怕……种种情绪,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他淹没。
他无法想象,如果毛泽东倒在这片阵地上,将会给这支已经岌岌可危的军队,带来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彭德怀心急如焚,准备不顾一切冲向河滩地时,一阵截然不同的枪声,突然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响了起来。
那枪声,清脆而急促,来自腊子口隘口的……后方!
是山顶!
奇袭分队成功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巨大的狂喜涌上了心头。
彭德怀猛地回头,望向敌人的碉堡。
只见原本嚣张的敌人阵地,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从背后射来的子弹,让他们措手不及,火力瞬间减弱了大半。
机会!
彭德怀甚至来不及下达命令,只是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震彻山谷的怒吼:
「司号员!吹冲锋号!给我冲上去!」
「嘟——嘟嘟——」
嘹亮而激昂的冲锋号,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骤然响起。
那是胜利的号角,那是绝地反击的呐喊。
所有还活着的战士,都像是被注入了一股神力,他们从战友的尸体旁爬起来,端着刺刀,眼中闪烁着复仇的火焰,向着那座象征着生门的独木桥,发起了最后的,也是最决绝的冲锋。
10
战斗,在天色微明时结束。
当胜利的红旗插上腊子口主碉堡的那一刻,整个峡谷都沸腾了。战士们互相拥抱着,欢呼着,许多人流下了滚烫的泪水。
他们,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挣扎了回来。
彭德怀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他带着警卫员,疯了一样冲向东边的河滩。当他看到毛泽东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只是军帽上多了一个弹孔时,积压了一夜的情绪,终于彻底爆发了。
「胡闹!简直是胡闹!」
他冲到毛泽东面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咆哮。
「你是政委!是党的领袖!谁让你带头冲锋的?你的命是自己的吗?你要是出了事,这个担子谁来扛?!」
面对彭德怀的怒火,毛泽东只是笑了笑,递给他一支烟。
「德怀同志,消消气。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他指了指身后不远处,那里,警卫排的战士们正在清理战场。河滩上,倒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
「我看到正面进攻压力太大,就想着从侧面,给敌人再施加一点压力。没想到,还真摸掉了一个暗堡。」他轻描淡写地说道。
彭德怀看着他,看着他脸上从容的微笑,和那顶帽子上惊心动魄的弹孔,一肚子的火气,却不知怎么,一点点地消散了。
他知道,毛泽东不是在胡闹。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位政治领袖,用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与所有的普通士兵站在一起,同生共死。
这种身先士卒的勇气,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政治动员,都更能鼓舞士气。
彭德怀接过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呛得连连咳嗽。
半晌,他才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下不为例。」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好,下不为例。」
11
攻克腊子口,为中央红军彻底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几天后,陕甘支队抵达哈达铺。在这里,彭德怀从一张旧报纸上,第一次得知了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根据地的确切消息。
这个消息,让全军上下为之振奋。
长征,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35年10月,部队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意味着,历时一年,纵横十一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为了庆祝这次伟大的胜利,也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最后一次“围剿”,彭德怀亲自部署,指挥部队在吴起镇外围,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切尾巴战斗,全歼了国民党马家军的一个骑兵团。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来到前线看望彭德怀。看着风尘仆仆、依然一身硝烟味的彭大将军,毛泽东豪情满怀,当即吟诵了一首六言诗相赠: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后来传遍了全军,也成为了彭德怀一生最光辉的写照。
“唯我彭大将军”,这不仅仅是对彭德怀赫赫战功的最高褒奖,更是对他在这段最艰难、最关键的征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勇于担当、敢打硬仗的革命精神的由衷赞叹。
站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回望来时的路,彭德怀感慨万千。
他想起了一路上与他并肩作战的那些搭档们。
杨尚昆的沉稳,李富春的热忱,刘少奇的深刻,叶剑英的周密,以及毛泽东那洞穿历史的深邃目光……
是他们,在自己脾气火爆、猛打猛冲的时候,给予了最及时的提醒和补充;是他们,在政治方向和战略大局上,为自己这把战刀,指明了最准确的方向。
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固然可以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但一支伟大的军队,想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就必须拥有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最完美的将帅搭档。
彭德怀是幸运的。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中国最顶尖的头脑。
而历史也证明了,这些在战火中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搭档们,最终都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正国级,对于他们而言,仿佛只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12
许多年后,当硝烟散尽,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彭德怀元帅,位列十大元帅次席,他那横刀立马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军史之上。
而他的那些老搭档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杨尚昆,成为了国家主席。晚年的他,依然时常追忆起与老总并肩作战的岁月,言语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李富春,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叶剑英,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展现出非凡的判断力和决策力,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刘少奇,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为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毛泽东,则作为一代伟人,带领着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这些闪光的名字,与“彭德怀”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的“军中地位”,并不仅仅由战功和军衔来决定。它更体现在,你与谁同行,与谁搭档,共同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彭德怀的特殊性,正在于此。
他不仅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元帅,他更像是革命洪流中的一块坚硬的基石。在他身边,总能凝聚起最强大的力量,从而去战胜一切看似不可战胜的敌人,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们是战友,是同志,是生死相依的搭档。
他们的每一次合作,每一次争论,每一次抉择,都深深地镌刻在了共和国的年轮里,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深深回味。
【参考资料来源】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 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王树增 《长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南配资-实盘杠杆配资平台-配资平台下载-国内大的证券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最安全的杠杆炒股平台官网触控式操控带来流畅简便的操作体验
- 下一篇:没有了